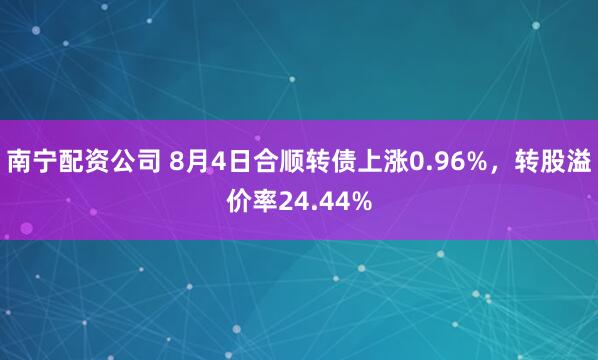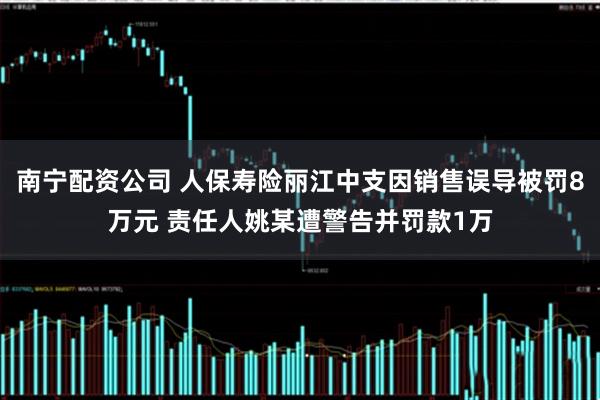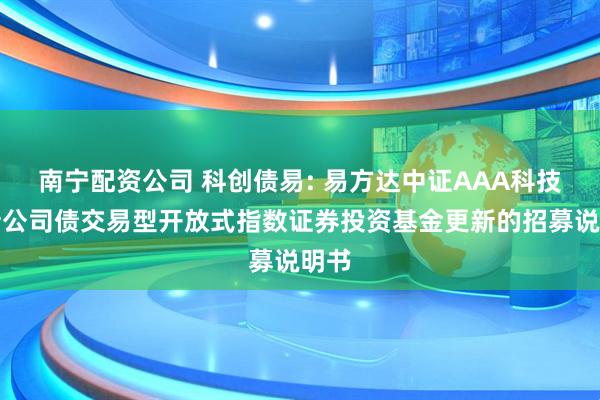流光倾泻的
庭院
——我在电影学院
图书馆的二三事
大一期间,我总是图书馆的常客,也总是在闭馆之际才离开图书馆的那个。那天,我在图书馆三楼,在几柜子的漫画书旁边,戴着耳机看到《少女革命》剧场版的末尾,欧蒂娜和安希紧紧相拥时钢琴曲奏响,电影的终末也是图书馆的一天又结束的日子——是的,钢琴曲正是图书馆闭馆的曲子,《流光倾泻的庭院》。而作曲家寺原孝明又恰好是寺山修司天井栈敷戏剧团的成员,为《再见箱舟》、《死者田园寺》等作曲。而《少女革命》的导演几原邦彦又恰好是寺山修司的粉丝,他也是《美少女战士》、《回转企鹅罐》的日本动画业界大拿……一首歌串联起了无数的思绪:在图书馆,每一本书,每一首歌,每一个人都是紧密相连,能诞生无穷无尽的关系的。“真不愧是电影学院选的图书馆闭馆曲啊,这都能致敬电影!”我想。而思路到这以后,我只觉得能够坐在图书馆,没有负担、没有焦虑,只带着求知的热忱读任何自己想读的书的自己,实在是无比的幸福。
展开剩余66%图书馆于我而言何尝不是一个流光倾泻的庭院呢?从大一入学慌慌张张地拿着水进馆被提醒“不能带食物喝饮料”时这种基本规矩都不懂的状态,到不知不觉成了借阅榜单的常客,图书馆已经是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一开始,我连借阅的字母排序都看不懂,搜索到某一本书只能笨拙地按照“某排某列”按图索骥,结果只能羞怯地向管理老师们陈述找不到书的窘状;再到后来,借阅的一些铁皮封面书总是刷不上,需要整个面摊开在扫描区域艰难地比划着才能找到扫描码,而每次救我于水火之中的依然是图书馆亲切的管理员们……大一的时候这几位老师端庄地坐在那里好像图书馆威严的门神一般,让我好生忌惮;而在图书馆待久了才发现老师们对学生和图书是多么的细致入微。按排序做好的分类十分科学、仔细,关于图书的知识架构清晰明确,甚至可以说,我对图书管理学的认知就是在逛学校图书馆的时候逐步建立的。
作为电影学系的学生,整个二楼全部都是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杂志合集的“圣状”,让我像一个掉进米缸的老鼠——电影学院老师的教材和著作、剧作理论与导演访谈集,大到史学编纂大合集,小到硕博论文无所不有……看到景仰的学者、思想家、导演、演员的名列映入眼帘,真的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如果北京电影学院的图书馆可以对外开放,那绝对是比库布里克书店、豆瓣书店还要令电影迷和文艺青年们向往的圣地。电影学院的图书馆也能满足“媒介考古”的癖好,当翻到80年代世界电影杂志中中国电影学者翻译的法国人和苏联电影人的采访时,改革开放初期学界吸收外来知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知识分子精气神真的扑面而来,里面还有很多豆瓣上根本搜不到条目的电影剧照和导演采访,如此珍贵的史料伴着书页的昏黄静静地按照年代陈列着、躺在那里,只是站在那的一瞬就仿佛看到了电影学院学术工作度过的四十余年春秋。
尽管在怀柔校区学习,海淀校区的图书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哲学、文艺理论书籍陈列就足以令人慨叹电影研究所需的学养深厚。再往里走就是文学书籍:从畅销网文到诺奖作品再到清代小说、唐宋传奇、各色各样的文学素材令人目不暇接;右手侧是名留青史的著名导演,望着那些导演或拍摄电影或领取奖杯的时间定格,便能切实感受到电影学院对于电影媒介的坚守;除开体裁严肃的书籍以外,你还能在海淀校区图书馆找到法国电影手册、香港电影的场刊,化妆手法大全,造景方法全论,乃至最新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杂志……一切都应有尽有!还书时最让人惊异的是“自助还书机”的便捷,相隔五十公里远的校区竟然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实现畅通无阻的借还书。
虽然自称为“嗜书如命”,总觉得有点自傲从而不免羞愧,但是何以弃书、谁能弃书?阅读就是任由文字在头脑的操场中驰骋,而不把这些阅读的过程记下来实在是可惜。如同弹簧一旦被压住就会失去弹性,如果不把我在图书馆的这些趣味记录下来,我读过的书、在图书馆里经过的岁月也就难以留下痕迹。如今,很多学校的图书馆已经“沦为”了普通的自习室:你看不到读书的人,只能看到为论文、PPT和考试而奔波的人。而一想到电影学院的图书馆竟能如此包罗万象、坚守着人文社科的一方阵地,不禁令人感动——数代电影人都试图在电影中创造、把握、捕捉这整个世界,我们关于世界的连接就这样在镜头的拍摄和剪接中建构起来。岁月蹉跎,但我并不觉得在图书馆里的时光有被浪费,它始终是我甘之如饴的流光倾泻的庭院。
上文来自电影学系申畅
提供的图书馆感悟南宁配资公司
发布于:北京市建宝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